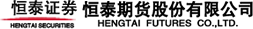我国《刑法》涉及洗钱规制的条文有三个,分别是:
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
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第三百四十九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
由于三个条文在文字表述上存在一些交叉重叠,相互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竞合关系,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分歧和适用障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三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或者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我们认为,这一规定表达不够详尽,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使人忽视犯罪构成进而直接“择一重罪处罚”武断处理案件。
那么,上述三个罪名在实践中如何区分适用呢?
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与适用
当上游犯罪行为属于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毒品犯罪等7种犯罪时,由于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的特别条款与一般条款的关系,就可以考虑适用洗钱罪,但并不是说只要掩饰、隐瞒的是7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构成洗钱罪,这里还需引入另外一个概念,即行为的方式和性质的问题,进而更深一步论证。
在罪状表述时,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使用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使用的是“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根据立法本意推敲前述罪状的措辞和表述可知,洗钱罪的行为方式是对(7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所进行的漂白、转换等资金性质上的改变行为,这种行为旨在使原本不合法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发生化学变化,使其表面上合法化,即把黑钱洗白。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方式当然的包含前述洗钱性质的行为,同时还有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所进行的窝藏、转移等空间位置上的改变行为,这种行为是在不改变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本源状态的情况下对其予以藏匿或流转,属于物理空间上的变化,目的在于逃避司法机关查处,并不具有使其表面合法化的特征。
据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洗钱罪的行为方式。
在明确这一概念后,罪名区别变得显而易见:
01.
对7种特定上游犯罪的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漂白、转换等掩饰、隐瞒行为的,构成洗钱罪。
其中,如果是实施了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此类掩饰、隐瞒行为的,应对其以上游犯罪和洗钱罪(自洗钱)数罪并罚;如果是本犯以外的他人明知是7种特定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仍实施此类掩饰、隐瞒行为的,则应对其以洗钱罪定罪处罚(排除其与本犯共同故意实施上游犯罪情形)。
02.
对7种特定上游犯罪的所得及收益实施藏匿、转移等掩饰、隐瞒行为的,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其中,如果是本犯以外的他人明知是7种特定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仍实施此类掩饰、隐瞒行为的,应对其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如果是实施了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此类掩饰、隐瞒行为的,由于目前《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尚未规定“自窝赃”行为入罪,且对于犯罪行为人的掩饰、隐瞒行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此应当认定此类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应予以定罪处罚。
如果当上游犯罪行为属于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毒品犯罪等7种犯罪以外犯罪时,此时由于适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种类前提并不存在,因此没有洗钱罪的适用空间。
对于此类犯罪的所得及收益,无论是针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所实施的漂白、转换等掩饰、隐瞒行为,还是针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本身所实施的窝藏、转移等掩饰、隐瞒行为,均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即可。
洗钱罪与窝藏、转移、
隐瞒毒品、毒赃罪的区别与适用
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罪状表述是“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
结合前述分析可知,该罪状将本罪的行为方式限定为窝藏、转移、隐瞒,属于前述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掩饰、隐瞒行为,不涵盖改变毒品或毒赃来源和性质的化学性质意义上的掩饰、隐瞒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犯罪对象为毒品或毒赃时:
01.
如果行为并非贩毒分子自身实施的窝藏、转移等掩饰、隐瞒行为,则构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如果行为是毒品犯罪分子本人实施的,仍属“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应予以单独定罪。
02.
如果实施的是漂白、转换等掩饰、隐瞒行为,则构成洗钱罪。当然其中也要区分,“他洗钱”要定罪处罚,“自洗钱”则数罪并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与窝藏、转移、
隐瞒毒品毒赃罪的区分与适用
当犯罪对象为“毒品、毒赃”或“毒品犯罪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有鉴于需要优先适用特别条款的原因。